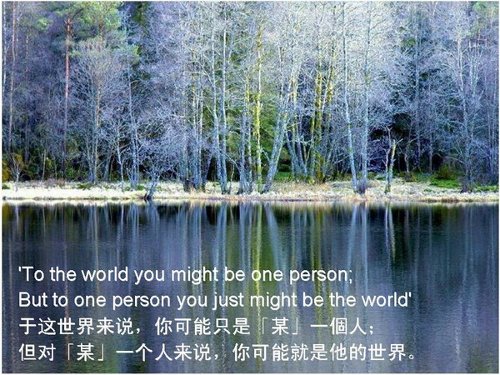
我高三时的语文老师名叫吴志文。
吴老师是南方人,因吴侬软语之音难改,成就了满口的南腔北调,我们姜堰人称之为“蛮子”。一日,吴老师又被人唤作“蛮子”,于是,愤愤然:你们姜堰人叫我们南方人“蛮子”,叫北方人“侉子”,你们自己呢?——杲昃!一语定乾坤,此后,再也没人当面叫他“蛮子”了。(注:杲昃是我们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方言词汇,无论天南海北,只要你知道杲昃为何意思,便可视为我们的同乡。)
高三的第一节语文课。铃声刚过,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便不紧不慢地踱进了我们教室。放下书,微仰着头,尖着嗓子,晃着两根手指,操着很怪的语调宣布:“下面:我们来——讲——上——一——通——”,“通”字被拉得很长,那腔调好似我们故意捏着鼻子发出的怪声,那声响就在大家即将发出“嗤嗤”笑声时猛地收住,但手指依旧在晃,这时大家才发现,这位新语文老师的一根摇晃的手指上缠着纱布,眼镜的镜片上也贴了半张膏药。滑稽的形象引来一阵骚动,也引出了吴老师的自嘲:“昨天晚上与老婆干仗,光荣负伤了……”全班哄然大笑。
我的高三第一节语文课就这样热烈开幕了。
吴老师总是慢条斯理的做着事。他慢条斯理的宣布每节课的开始,“下面,我们来讲上一通”是他始终如一的开场白;他慢条斯理的在黑板上一笔一划的书写,我们惊讶于他的字刚正风流洒脱,一丝不苟;他慢条斯理的给我们讲作文,从遣词造句到谋篇布局再到立意升华,使我这个只会“挤牙膏”人也能写出通顺的文字,为日后混进语文教师队伍打了点基础;他慢条斯理的讲着他独有的幽默,任你笑得前仰后合,他只会不笑且一脸的无辜;他慢条斯理的讲着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将“相亲、爱情、相爱”等字眼故意用“那个”来替代,并且故意拖着长音说“他们——那个”,而他在课堂上也津津乐道于谈论“那个”,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,搞得有些同学不禁神往起来。
我只见过他发过一次火,是咬牙切齿眼中冒火涨红了脸的那种,其他任何时候,他总是微微上扬着下巴,倔强而不屑地从眼镜片的下沿看着对方,因此,成绩一直属于“贫下中农”的我,几乎没有理由与老师亲密接触。
二十多年后,我在励才学校的专家办公室里与吴老师不期而遇。这么多年了,吴老师居然认识我,还叫出了我的姓和名,并且关切的询问我的近况。这之后,就再也没有遇过,不知先生是否已远渡重洋,与远在美利坚的女儿在一起?
任教我高一高二语文的是丁仁山先生,吴志文老师只教了我一年的高三。即便这样,吴老师的沉稳幽默,丁老师的开朗坚强却没有随时间被我淡忘。在这个属于所有教师的节日里,我突然想到了他们两个,只愿他们两个永远开朗坚强,永远沉稳幽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