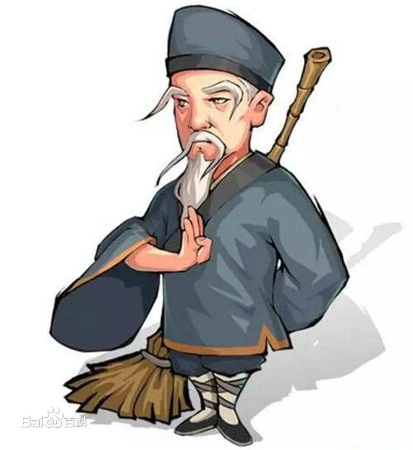好几个月不写一个字,公号上次的更新还在《板书留存》那儿。
我停在那儿了。
就像一台机器被按下暂停键,它停止了运动。但人毕竟不是机器。当一个人给自己暂停一下的时候,他就重新开始了。他开始反思,开始重新思考,开始以一种新的角度重新设想什么事是可能做到的,最重要的是,他开始与内心深处最坚定的信仰重新建立联系。
我停在那儿了。
我正准备着要“迟到”。
刚刚,我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姜堰最繁忙的地段,坝口整条街都有人吆喝:“不要穿线的针!不生锈的针!”我从人群、车流中挤出来,脑袋却还停在那几声吆喝声中——还有不要穿线的针?这不是给我这种高度近视的人提供巨大便利?是真还是假?骗子吧……唔,世界变化太快了!当世界变快了之后,脑袋跟不上了。速度并不总是带来激情,速度也会带来眩晕。这种眩晕,就是我们越来越焦虑的罪魁祸首。
我似乎越来越不会与自己相处,不会与世界相处。做教育的人都知道,教育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,教育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,人与自我的关系,人与他人、与社会、世界的关系。有人说,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“变”,我以为,还有一个不变的,就是“人”。世界速度再快再智能再便捷,终究离不开“人”。当我发现自己没法与世界和谐相处时,我知道,我真的该停下来了。苏轼那句“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,算来著甚干忙。事皆前定,谁弱又谁强。且趁闲身未老,尽放我、些子疏狂。百年里,浑教是醉,三万六千场。”他在政治场历经坎坷,总算得以清闲,停下来去尽享“千钟美酒,一曲满庭芳。”
年少时,一旦停下来,就会追问自己:我该何去何从?
人到中年,停下来,轻轻道一声:我还在这里。
十四年前踏上讲台,学校送来苏霍姆林斯基的《给教师的建议》,那时,一心想从书中得到教育教学知识,每个篇章都想摘抄咀嚼。十四年后还在讲台,停下来,重新翻阅此书。早已没了当初那种“我要得到”的功利念头,每一篇章却足以让我感动,甚至感恩遇见这些文字。
且看此段:我们当教师的人应当记住:对每一个学习困难的儿童来说,不管他已经被耽误到了什么程度,我们都应当让他在公民的、劳动的、精神的生活道路上站住脚,我们的崇高的使命就在于:要使我们的每一个学生选择这样一条生活道路和这样一种专业,它不仅是供给他一块够吃的面包,而且还能给予他生活的欢乐,给予他一种自尊感。
教育在寻找“人”,给予快乐,给予自尊感,我们又有多少低头赶路的老师、家长可以做得到?
没有了学以致用的心,反而能够常常越过工具价值,得到背后的浓浓诗意。停下来,功利心淡了,审美的敏感度自然浮现。佛家所谓“担水劈柴,无非妙道”,《天龙八部》里那个扫地僧,放到世俗的场景里,或许就是这个道理。